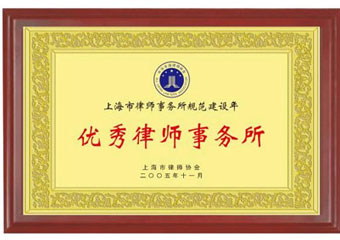案例:被告人賈某某和他人共同出資在深圳市注冊成立某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深圳公司)。自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深圳公司均從開設于北京市的某防水材料公司(以下簡稱北京公司)賒購防水專用材料用于工程建設。深圳公司與北京公司通常不定期對賬、清償貨款。賈某某所在的深圳公司在陸續收回材料款并向北京公司返還欠款過程中,賈某某個人向北京公司提出:原本應由深圳公司支付給北京公司貨款中的381萬元,其個人要借來用一段時間。對此,北京公司負責人明確表示同意,該款便從賈某某擔任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公司轉入賈某某個人賬戶由其個人使用。但是,法院認定賈某某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數額較大,超過3個月未還,構成挪用資金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
深圳律師指出挪用資金罪是實踐中的常見罪名。一般而言,直接改變本單位的財物控制權的挪用資金行為不難認定。但是,在案件涉及多個民事主體時資金究竟歸屬于誰,對于本罪的認定會產生實質影響。因此,認定本罪時需要顧及民法的立場。

控方認為,在被告人賈某某轉移資金時,該款所有權仍屬于深圳公司,并未轉移到北京公司名下,因此其構成犯罪。被告人認為,該筆資金是其以個人名義向北京公司的借款,其也向北京公司出具了相應欠條,同時北京公司不再要求深圳公司支付該筆貨款,因此被告人無罪。由于本案的處理摻雜了對民事法律問題的判斷,就應遵循法秩序的統一性,防止將前置法上不具有違法性的行為在刑法上認定為犯罪。對于法秩序統一性原理,在與本案有關聯的意義上絕對不能偏離的規則是:在民法上合法的行為,不可能成為刑法上的犯罪;唯有民法所要反對的行為,才有可能成為犯罪行為。因此,對于涉案381萬元資金的性質必須回歸民法規定進行理解,而不能在刑法上想當然地進行民事法律關系設定。
處理本案繞不開民事上“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這一問題。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由第三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第三人不履行債務或者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的,債務人應當向債權人承擔違約責任。”這是關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規定。所謂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是指雙方當事人約定債務由第三人履行的情形。例如,甲、乙約定:甲應當支付給乙的金錢由第三人提供給乙。“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往往具有減少交易環節,提高交易效率的功能”。
在本案中,賈某某和北京公司就382萬元達成借款約定,北京公司根據這一約定有義務向賈某某支付金錢,在提供借款(借款給付)這一環節,北京公司成為債務人,有權獲取借款的賈某某成為債權人。北京公司、賈某某作為借款合同的當事雙方,約定由第三人深圳公司履行該項381萬元的給付,就屬于典型的“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情形。
本案“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明顯特點是:
01、針對381萬元的借款合同在債權人(賈某某)、債務人(北京公司)之間訂立,他們才是合同當事人,第三人(深圳公司)不是合同當事人。第三人(深圳公司)向獲得借款的債權人(賈某某)履行債務的具體原因如何以及賈某某是否實施了違反公司法的背信行為,均不影響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02、合同標的是第三人(深圳公司)向債權人(賈某某)的履行行為。根據合同相對性的原則,第三人(深圳公司)雖不是合同雙方,該合同對其沒有約束力,但其一旦向債權人(賈某某)履行合同,其和具有供銷關系的債權人(出借381萬元的債務人)北京公司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就歸于消滅。
03、第三人(深圳公司)履行合同后,債權人(賈某某)即對資金出借人北京公司承擔還款義務。
由此可見,就本案被告人賈某某與北京公司借款合同的履行而言,該筆381萬元資金從深圳公司轉到賈某某名下,且北京公司在與深圳公司核算債務時已經將欠條中的381萬元扣除,這意味著雙方對賬時北京公司已經認可深圳公司償還了該筆貨款,其實質就是北京公司指令作為第三人的深圳公司直接向債權人履行債務。因此,涉案資金雖然并未先從深圳公司名下轉至北京公司名下,再由北京公司轉至賈某某名下,但實際上已經通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完成了借款過程。
如此說來,本案要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結論是有難度的。從客觀上看,在賈某某與北京公司之間達成借款協議之時,該筆由第三人深圳公司所提供資金的法律性質就發生了轉變。北京公司一方面完成了相應的出借資金義務,另一方面在記賬單中也放棄了對深圳公司381萬元進貨款的債權。因此,該筆381萬元資金自轉入之時起就屬于被告人賈某某所有,不再是深圳公司的資金,賈某某后續有權處分自己的財產,不存在挪用深圳公司資金的問題。從主觀上看,由于借款合同真實有效,被告人賈某某始終認為涉案資金是自己向北京公司的借款,其不屬于明知是本單位的資金而非法占有、使用,不具有挪用資金罪的主觀故意。
本案判決的不當之處是片面理解了合同履行問題,機械地強調合同只能在簽約當事人之間“直接履行”這一點,認為涉案381萬元資金必須遵循“深圳公司——北京公司——賈某某”的轉款進路,即先轉出再轉入,才能既實現深圳公司向北京公司的債務清償,又滿足賈某某個人向北京公司的借款需求等法律效果。因此,判決是立足于合同必須“直接履行”這一點對被告人定罪。但是,民法上所認可的合同履行方式除了由債務人直接向債權人履行之外,還有為了減少交易成本的“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這一類型。
因此,對本案的定性必須考慮的是:根據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條的規定,深圳公司自履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之日起,其和北京公司的債權債務即告消滅,即便賈某某未來不履行該還款義務,北京公司也無權再向深圳公司主張該筆款項。本案對被告人不予定罪與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三條的內在精神相一致,既然北京公司已經同意借款381萬元給賈某某,該款實質上就是北京公司向賈某某發放借款之物;深圳公司向賈某某交付381萬元的同時其與北京公司之間的相應債權債務履行完畢。深圳公司實質上的還款行為談不上使其381萬元失去控制,更談不上其由此遭受財產損害。
因此,在民法上認可第三人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刑法上認定接受第三人履行合同所提供之物的行為構成犯罪,明顯與民法立場相抵觸,違背了法秩序統一性原理。 深圳律師事務所